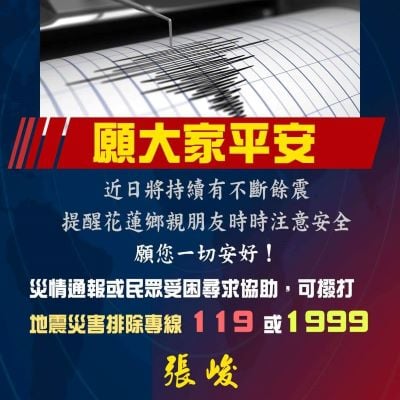「性侵害」犯罪證據的取捨,到底多困難?

性侵害案件常常是法官們最傷腦筋的案件類型之一。原因在於犯罪現場往往只有加害人和被害人,地點大多隱密到底是雙方合意或一方強制,事後各說各話,很難有目擊證人可以證明整件事情,再加上涉及性的案件的受害者為了避免二度受到傷害、出於徬徨或羞恥感,或其他理由,被害人往往沒有在當下就前往醫院等驗傷,使得性侵害案件證據很難呈現完整全貎。然而,性侵犯罪法律規定的刑期都很重,一般來說也很難找到減輕的理由(或許和解多少有幫助)。
性侵害案件的證據,一般都只有告訴人(即被害人)單方指證,
尤其性侵害案件的要件強調「是否違反對方的意願」,很少有人會公開、公然的在第三人面前為性侵害行為 或留下白紙黑字證明整個過程。陌生人的性侵害,使用藥劑或暴力的可能性很高,在蒐證上相對比較容易,可以去醫院驗傷或被保留DNA當作證據。但朋友、同事、戀人、夫妻之間的性侵害,只有兩個人在場,證明的難度就非常高,被告往往會以「對方是自願的」的說法,來掩蓋性侵害的事實。可是法律規定被害人單方指證,不能作為判決唯一證據,還要有其他「補強證據」。而這類案件,通常不是案發當下即訴諸司法,而是經過長時間的煎熬,突然在一個引爆點,例如:媽媽無意中發現,學校老師上性別教育或社工做家庭輔導等等的時候,才講出來,因為時過境遷,證據都不存在,媽媽、學校老師和社工也只能證明被害人跟他(她)們講過這件事,至於此事的真實性為何,並不能由學校老師和社工口中獲得證明。這時候只有將被害人送專業鑑定,但時間已經經過許久,鑑定得出來嗎?鑑定結果會讓人信服嗎?況且,鑑定報告只是在評估被害者的心理狀態,頂多也只是被害人指證的延伸,是「累積證據」而非「補強證據」。尤其,兒童、智能障礙者被性侵害的案件,他(她)們的認知及表達能力,一般較常人差,前後矛盾、反反覆覆,又容易被旁人誘導,所作的陳述何者是真、何者是虛,更是難上加難!
2010年8月15日最高法院一件有關於性侵害女童案件的判決引發「白玫瑰運動」,這場運動帶來的正面效益,就是對於性侵害受害者(特別是孩童)的正視,重視他們有口難言不願面對過往的反覆傷害。這場運動的結果,人民要求法官判決要能符合社會期待,稍有不滿動輒辱稱「恐龍法官」。在這樣的氛圍下,司法實務上確實有些若干詭譎的改變,法官為了顧及社會觀感,自行降低證據證明力的強度,在性侵害案件中被指控的一方,幾乎可說是「有罪推定」,除非被告能夠提出非常明確的反證,否則很難脫身。「無罪推定原則」在性侵害案件領域,似乎變得蕩然無存!
「無罪推定原則」在刑事審判裡,法律上要求要具有相當程度的「證據證明力」才可以定罪。換言之,如果蒐集到的證據都沒有辦法證明一個人有罪,就應該認為被告是無罪的,而證據的證明力要達到「無合理懷疑」的程度(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所以,過往許多性侵害案件判決無罪的理由,多是:被害人供述前後不一有瑕疵可指、被害人供述與其他客觀證據或其他證人證述情節不相符合、被害人與行為人有過節恐有挾怨報復或捏造誇大供詞的可能、被害人智慮淺薄思慮單純供詞受到外界污染或誘導、專家鑑定報告超越其鑑定專業不可採等等。但觀察近來的判決,法官似乎已經降低證據證明力的強度,所以:供述前後不一應係時間經過久遠細節記憶不清楚所致、若非親身經歷其事且記憶深刻,怎可能將被害細節鉅細靡遺陳述、證人陳述被害人告知被害情節時表情痛苦或低頭啜泣或呼吸急促或欲言又止等情狀,適足證明被害人曾有經歷其事,才會深受創傷尚未平復、性犯罪涉及個人隱私名節,易招致異樣眼光,在社會規訓下仍願挺身而出揪出犯罪者,設詞誣攀的可能性不高等等。這猶如刀之兩刃,要看鋒利的一邊還是滯鈍的一面,如果裁判者主觀上已經將站在法庭的被告「定錨」是行為人,再多證據的呈現也會偏向不利的解讀!裁判者內心若有太多的社會正義包袱,失去心中的天平,想像自己是正義魔人,有利的證據很可能會被忽略不見,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反而變得卑賤低微。或許整個訴訟程序的參與者大家都沒有惡意,但很可能因此會讓一個無辜的人身陷囹圄,讓一個幸福的家庭就此破碎沉淪!
作者 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花蓮地方法院法官退休、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